「边疆时空」李沛容|民国时期任乃强的边疆民族观及其嬗变
发布日期:2024-09-16 17:19
来源类型:潮句子 | 作者:別所哲也
| 【494949澳门今晚开什么】 【2024新澳免费资料】 【澳门六开彩资料查询最新2024】 | 【澳门金牛版正版资料大全免费】 【新澳开奖记录今天结果】 【2024年新澳门王中王资料】 【管家婆最准一肖一码】 【新澳彩开奖结果查询】 【2023澳彩资料免费大全】 【4949澳门免费资料大全特色】 【2024今晚澳门特马开什么号】 【今晚精准一肖一码】 【2O24澳彩管家婆资料传真】
原文标题:《“中华国民之一体”: 民国时期任乃强的边疆民族观及其嬗变》
李沛容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题 要:近代内忧外患的时局促使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内地知识精英与边疆民族的交往互动对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起到积极作用。文章尝试运用“知识史”“概念史”等方法,从个人生命史的视角,探讨任乃强如何超越传统的“华夷秩序”观,以边疆民族为“主位”,重新思考边疆民族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并探索与思考“中华国民之一体”的内涵。
关键词:任乃强;边疆民族;“主位”;“中华国民之一体”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探索中指出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变,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内地知识精英与边疆民族的交往互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探索起到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华西学派”的学者因地缘优势,较早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本文以“华西学派”代表人物任乃强的边疆民族研究为中心,尝试运用“知识史”“概念史”等方法,通过梳理任乃强的个人生命史,探讨其如何超越传统的“华夷秩序”观,以边疆民族为“主位”,重新思考边疆民族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关系,并探索与思考“中华国民之一体”的内涵。
一、跨越“华夷秩序”:民国时期任乃强边疆民族观的变化
1894年任乃强出生在今四川省南充市,五岁时入乡塾受童蒙启迪,1906年科举制废除后转入高小就读,至1915年考入北平(今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接受近代新式教育。为探寻建设具有内在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近代政界、学界的普遍逻辑是将西方的“民族”“种族”概念与中国传统“华夷秩序”观念相互调和,来达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目的。在这一话语体系下,边疆民族固有的社会文化相对受到忽视。任乃强的早期论著也深受时代观念影响。1929年,受大学同窗胡子昂(时任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处长)邀请,任乃强前往西康从事垦务调查工作,开始与边疆结缘,成为民国时期康藏问题研究的先驱之一。第一次入康之行后,任乃强撰写的著述如《西康诡异录》《西康札记》等,均受到传统“华夷”观念与近代社会进化论的双重影响,较为注重汉族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在《西康图经》中,任乃强提出六项建议,旨在消除因“道路梗塞”“文语隔阂”造成的差异,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这些建议往往被学者误解为任乃强早年纯粹是以“汉文明为中心”审视边疆民族。但是仔细梳理史料发现,将之简单归入“汉化论”并不恰当。
在相关论述中,任乃强对“汉文化”同样抱持着审慎态度。1929年初入西康途经丹巴时,任乃强便发现彼时入康汉人同样夹杂着“嗜烟好讼”“心地艰险”者。他在稍后的著作中进一步阐释上述观点:
往时入康汉人……或属商贾小贩,或为军台胥役,或流亡充配之徒。绝少文士通人也。即如官吏,亦以纳捐入流者为多。故段玉裁曾官化林,姚莹曾至乍丫,杨揆曾入西藏,李心衡曾宰金川,余如果亲王、查礼、孙士毅、王我师等,匆匆一过,偶有题咏,便成千古韵事。赵尔丰时,边局全盛,得人较多。查所调用官吏59名中,只进士1名,举人13名。此外乡试副榜2名,贡生10名,增生1名,附生3名,监生18名,学校毕业者5名,无资历者6名。其幕府中,自总文案傅嵩炑以下,皆吏材而非文学之士。曾聘井研吴蜀猷入康举学,备极礼重,在当时边区得此,直如凤毛麟角矣。故康区汉人,虽有数万,其足代表汉族文化者,不过十分之一。言行表现,多不能使藏族发生景慕。
任乃强未曾言明,但从其所举案例中能看到让边疆民族发生“景慕”者并非汉文化本身,而是以饱读诗书、科举入仕者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在传统社会,崇尚和效仿儒家文化礼仪关系到威望的竞争,边疆民族精英往往也将这一儒家化进程视为“文明化”的标志。这便与明清时期要求边疆民族“易椎髻而冠裳”“男耕女织”“婚配媒妁”“济美华风”的“汉化”截然不同。任乃强认为上古时代的颛顼、大禹和启皆生于边疆,正因环境严酷艰苦,天赋“奋斗精神,沉毅厚重、锐志奋发”,“其成就往往较长于安乐环境之腹地人士为大”。在长期接触中,任乃强逐步以本位角度审视边疆民族,指出“蕃族”不仅有“佞佛、仁慈、从容、有礼、节用、爱物、矫捷、犷勇、乐天、安命、自尊”等固有美德,而且“于其特育之佛教文化中,成就伟大,足使五千年岸然自诩之汉人俯首称弟子者,尤多不胜举”,“是固不得不为伟大之文化,不得不为伟大之人物”。而彝族中也不乏知名人物,暖带田土司岭承恩“绘像紫光阁”,岭光电则“博识能文,多数汉人不逮之”。因此,任乃强认为理想的治边之道应该是“尽量发扬各族文化优长之点”,“使之交融”。在与边疆民族的不断接触与交往中,任乃强已然意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优劣,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构建实需发挥各民族的优势文化,促进彼此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抗战全面爆发后,边政学兴起,边疆成为各类学术流派的实践场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川康地区被视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西南边疆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学界在重新定位边疆地位和构建中华民族国族体系时,逐渐破除“华夷”之别,改变了传统“华”“夷”二分的认知逻辑。
在这一背景下,1943年任乃强辞去西康省公职后,赴华西协合大学任教。适逢李安宅任社会学系主任,推动边疆社会工作。任乃强遂以十余年的边疆实践经验为依据撰写《边疆垦殖与社会工作》一文,以学者身份重新阐释对边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此时,政界、学界对边疆概念的界定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即与外国接壤的内陆边疆区域;二是政治意义上的边疆,也就是奉行传统边疆旧制的特殊区域;三是文化意义上的边疆,侧重指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即使在内地也可视为边疆”。任乃强对边疆的理解不同于李安宅、吴文藻等主张的文化意义上的边疆,而是从政治层面加以解读,但是又与当时主流的政治意义上的边疆,即“推行旧日边政制度区域”有所不同。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度是任乃强区别边疆和腹地的主要依据,诚如其所言“不以吾国政化未能贯彻全领域为讳,则政化已能贯彻之地域为腹地,未能贯彻之地域为边疆”。如若政化全部推行,则“边地与腹地之对立名词,俱当消减”。消减对立的方式是促进“边民”与“腹民”一同转变为“现代公民”:
我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本自完整。惟所包含之人民,语文习俗,尚未一致,因而对于国家法令之了解力与推行程度,各地不同。如此未能了解国家法令之含义而热忱推行之者,称为边民。一区域中,边民占大多数者,称为边地。与此相反,边民占绝对少数地区,是为腹地,腹地居住之国民,依比例方法作一省称,似亦可呼为腹民。边民与腹民,皆我国家之公民也。所不同,仅在于是否已能达于现代公民水准。
任乃强强调“边民”与“腹民”具有达到“现代公民水准”的平等性。“移植腹民”的目的在于促进“边民”“现代公民化”。在这一视野下,任乃强痛斥“用夏变夷”的传统“华夷秩序”,“不问边民之生活习惯如何,一概以施于内地者施诸边疆”。这就难免造成“边民”对国家政令的误解,以及国家在向边地推行政令时遭遇的颇多掣肘。故此,为将“边民”纳入“现代公民”体系时,任乃强认为在行政层面,“边疆行政,与腹地行政,大经大法,可以相同;小处细处,决不可以从同”。而国家应当因地制宜,切实研究并推行适应边疆特殊性的法律、法规,将边疆问题特殊化处理。此外,任乃强建议在边疆民族聚居区设立垦场,以发挥如下优势:首先,“研究边民习俗信仰,政教之宜,推寻因势利导之术,贡献政府。以垦场为社会工作站,推行一切边民福利与合作事业,调协边民情感”,达到“化除民族畛域之目的”;其次,“以垦场为新社会之示范区,一切社会行政,悉依现代公民之标准施行”;最终,边疆社会追随垦场,“捷速进达于现代社会之新阶段”。任乃强理解的“政治上的边疆”与“文化意义上的边疆”虽有一定相似性,“边地”转化为“腹地”的核心均在于“民众”,但是“文化意义上的边疆”所具有的“他者”属性,在内化为“腹地”时势必需要借助“涵化”手段改变边疆民族的原有文化。而“政治上的边疆”可以摆脱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诚如任乃强对比上述边疆概念后指出,“政治上的边疆”“与住民之血统亦无关,陇西多回民,黔省多苗民,固不失为腹地也”。因此,对于国民意识的塑造、国族的构建无需改变边疆民族的固有文化,只需政令推行顺畅,即可实现变“边地”为“腹地”,变“边民”为“现代公民”的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目的。
二、“中华国民之一体”:任乃强边疆民族观转变的动力机制
抗战全面爆发后,基于对“边疆”属性的重新定位,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抛弃了传统“华夷”观念,转而提倡建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国族。学界的变化主要源自西方历史特殊论、文化相对论、功能主义等新兴理论的推动。长期以来,学界认为任乃强对边疆民族问题思考的转变源于1943年入职华西协合大学后,逐渐受到“华西学派”学者的影响。但是通过对比其主要论著的表述变化会发现,有关任乃强学术思想转变的上述解读实为一种误识。任乃强诸多重要思想的形成事实上奠基于任职西康期间。早在1940年任西康省通志馆编修主任草拟《西康通志稿撰修纲要》时,任乃强便流露出期望改变过去“华夷之辨”的成见,矫正“昔人漠视边民之习,而负总理民族平等之义”的想法,提出《西康通志》的撰写应当本着“研究精神”“平情叙述”的方式描述边疆民族的宗教、语文与习俗。回到成都后,任乃强深知学界对边疆概念的争议以及对国族认知观念的转变。但是其对边疆、边疆民族问题以及边疆民族国民意识的理解,得益于政务人员、学者等多重身份的实践及其与边疆民族的交游和交往经历。这一思想的集中表述是任乃强的妻子罗哲情错在国民代表大会结束后提出将边疆民族熔铸于“中华国民之一体”。这或许可视为任乃强边疆民族观转变后夫妇二人的共同倡议。
总体来讲,任乃强边疆民族观的变化,可以看作其多重身份转换下的学术反思。
第一,从政经历的体悟转化为以边疆民族为“主位”的学术思考。初次入康时,任乃强深知乌拉流弊积重难返,“民间闻乌拉,鲜不色变”。对于乌拉引致民困一事,任乃强如鲠在喉。1935年被刘文辉委任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时,任乃强提交《建议设立公运局办理牧站联运期能永废乌拉以纾民困而利交通案》。提案一再强调“徭役繁数,民不堪命”,“苟非设法彻底解决”,则“边民苦痛,终难减除”,建议以牧站联运制代替乌拉差役。任乃强指出西康藏族同为国家的国民,政府“释民重负”,方可“深得民心”。在1946年发表的《论边疆文化与其人物》一文中,任乃强又将上述从政时期的经历内化为治学的理论思考,运用比喻手法描述“国家”与“边疆”之间的关系,将“边疆”喻为“舟”,“政府”喻为“边疆之舵工”,“人民”喻为“边疆之橹手”,只要“政府与人民,通力合作”,得其道者,则“数十年可化边疆为腹地”。
第二,从地方性知识审视和反思边疆民族问题。自20世纪40年代初,任乃强在著作中放弃了传统文献对藏族的“蛮”“番”称谓,转而使用藏族自称“蕃”一词,这一称谓转变源自其早年在西康从事的吐蕃史研究。任乃强翻阅和对比大量中外文献后,发现新、旧《唐书》“吐蕃传”对于唐蕃边衅记载翔实,对吐蕃内情却“隔膜未通”,尚不如西人贝尔所著《西藏今夕》,寥寥数语间却将吐蕃“政治文化与兴衰隆替之迹,胪列指掌”。究其原因,贝尔“取材藏籍”,唐书仅“持汉文档册”。任乃强认为,“夫一民族文化,各自有其特质著作为文化之代表品”,而欲求知藏文化全貌,需要从藏文典籍入手,因而任乃强开始着手《西藏政教史鉴》的译注并考证“蕃”字一词使用原委。此外,1946年组织成立“康藏研究社”时,任乃强特别注意邀集和延聘谢国安、刘立千、任映苍等长期居于康藏、边疆知识丰富的学者,将麻翁倾真、夏克刀登、罗哲情错、革桑悦西、甲日宜玛、邦达多吉、岭光电等边疆民族精英列为理事或会员。成立“康藏研究社”的初衷之一就在于“吸收边疆土人之游历内地者于此,以为活动的研究资料,则一切死的资料皆可印证”。可见任乃强致力于理解和掌握边疆地方性知识的努力。
第三,长期的边疆实地考察经验促使其发现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趋势。早在初入西康途中,任乃强就发现道孚觉乐寺附近清代塘汛遗民与当地藏族形成了混处杂居的共生现象且文化和语言多受藏族影响。任乃强将此现象称为“康化”。在边疆社会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现象比比皆是。如同任乃强对比史料与田野经验后所言,近代康藏地区的浑脱(羊皮筏)、羊卜骨等均是蒙古族南下后的文化遗存。尤为重要的是,散处康藏山谷中虽为同源却分散隔离的人群在文化上渐趋统一,正是明末厄鲁特蒙古部在康藏地区传播藏传佛教的结果。宁属白彝也是汉族受彝族文化影响的实例。基于上述认知,1949年问世的《四川第十六区民族分布》一文可视为民国时期任乃强边疆民族研究的总结之作。文中详细分析了川西北藏羌地区多元的文化样态。通过长期的边疆问题研究,任乃强清晰地认识到川西北是高原游牧文化与平原农耕文化交往互动的重要场所。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融最终促使区域内各民族形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倾向。历史上文化强势的汉人进入此区域后同样逐渐受到藏族或羌族文化的影响。任乃强的思考源于对研究对象,即被后世称为“藏彝走廊”这一民族文化复合区域的深入考察。区域内呈现的多民族交往、互动现象促使任乃强提出发扬各民族的优势文化,促进民族交流与交融的主张。另一方面,基于对边疆多民族区域的认知与理解,任乃强认为在保留边地与边民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塑造边疆民族的“国民性”同样可以实现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
第四,族际通婚的生活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任乃强对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解。西康建省委员会迁入康定后,任乃强携罗哲情错入康并被刘文辉委任为宣化员。在沟通汉藏关系中,罗哲情错不遗余力,招抚甲日家、接待孔撒女土司以及组织藏族妇女会,并于1942年加入西康妇女工作会。罗哲情错展现出的参政意愿与政务能力及其边地实践经验,改变了任乃强过去认为康藏官吏“取自边地”,“未可胜任”,应“即早招致内地有志边疆青年”方为上策的最初观点。任乃强曾对罗哲情错谈及,“未来的康区官吏,必然是懂得汉情又懂得康情,说得汉话又说得康话,认得汉文又认得藏文的人”,那时犹如罗哲情错一般深谙汉藏语言文化的边疆人士便不乏用武之地。这些想法极可能融入罗哲情错向国民大会提交的《请以法律规定边民参政权益案》。罗哲情错在提案中提到,“是非有边民参加政府帮助其研讨设计,则措施难洽于边情”,而政府“诚能容许边民之先进者与我治边之士混处一堂,既可使得学习政治之机会,又可藉昭提携边民之至诚”。早在迎娶罗哲情错之初,任乃强便希望罗哲情错可以“宣泄西康民众之真实心愿于国民”。自1947年以来,任乃强鼓励罗哲情错与声援岭光电参选国大代表,便是希望实现边疆民族“现代公民化”的转变,实现边疆民族以国民身份参政议政、将边疆民情传达于国家的意愿,最终破除族际隔阂,真正熔铸边疆民族为“中华国民之一体”。
结 语
在历史文献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刻意寻求范式化的规律性解读往往会遮蔽历史存在的多样性与复调性。以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为例,奉行解构主义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民国中后期中国知识界结合传统史学考据与近代西方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虽然奠定了“中华民族多起源论”,但为服务于“国族一体性”的构建,其认知主体并未超越中原与周边、华夏与四夷、征服与被征服、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最终导向仍然是优势民族——汉族必然“同化”边疆民族的认知神话。从民国时期任乃强的边疆民族观及其嬗变过程来看,这一典范化、程式化的研究模式并不适用于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概括性分析。
此外,有学者提出,在建构“民族”与“国民”的双重话语下,随着边疆调查的深入,民族学者成为“民族”知识在边地的普及者与传播者,客观上成为民国时期边疆人群民族身份的塑造者。这一认知或许有意或无意地遗忘、淡化了两条重要的史实线索。首先,在长期的实地考察经历中,以任乃强为代表的民族学者发现边疆民族地区存在着多维度的文化互动与交融现象。基于此,任乃强认为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族际通婚,促进民族间的“人物交流”“语文交流”“文化交流”,进而发挥各民族的优势文化,形成中华民族优良的共有文化。其次,罗哲情错的案例并非孤证,近代以来藏族精英格桑泽仁、彝族精英曲木藏尧等边疆民族精英不断践行着其作为国民的义务,为沟通民族关系奔走呼吁、建言献策,积极跻身于国家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这些事例均是边疆民族精英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铺陈与展演。
诚如费孝通所言,中国各民族历经“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最终奠定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特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于频繁的互动与交往,近代边疆民族精英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无疑也投射、影响到汉族知识分子对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解与思考。边疆的田野经历、边疆民族精英的启示以及藏族夫婿的特殊身份促使任乃强越来越倾向以“主位”(emic)或“移情”(empathy)的方法重新审视研究对象。通过深度理解边疆民族文化,任乃强跳脱出传统的“华夷秩序”观,而罗哲情错、岭光电等边疆民族精英展现出的“国民”情怀,促使任乃强意识到边疆民族具有自觉的国民意识。有学者曾慨叹道,“建‘民族’易,造‘国民’难”。回顾历史,在内外交困的民国时期,以任乃强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以其边疆实践经验为“华西学派”乃至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对边疆问题的“主位”反思,深入发掘边疆民族自觉的国民性,仍不失为今天学界探索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份宝贵遗产。
【注】文章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1期。
责编:李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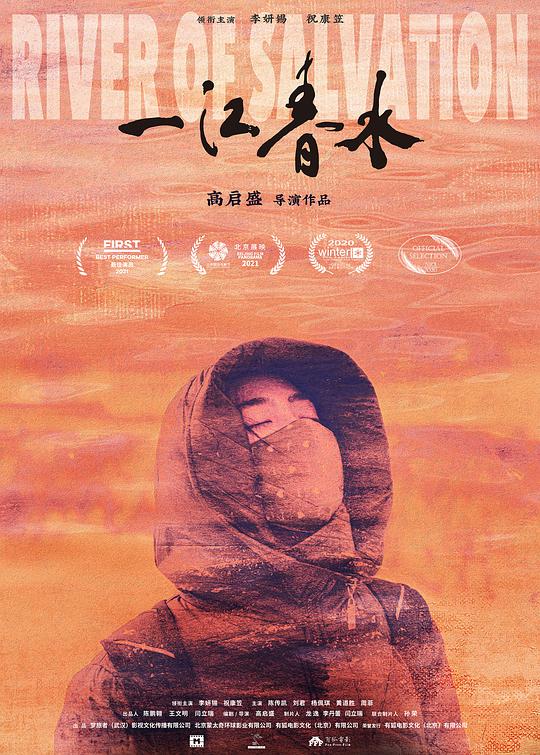
Deshmukh:
9秒前:回顾历史,在内外交困的民国时期,以任乃强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以其边疆实践经验为“华西学派”乃至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罗勃·梅耶斯:
6秒前:惟所包含之人民,语文习俗,尚未一致,因而对于国家法令之了解力与推行程度,各地不同。
早濑雪未:
9秒前:对于乌拉引致民困一事,任乃强如鲠在喉。
Dafoe:
1秒前:与此相反,边民占绝对少数地区,是为腹地,腹地居住之国民,依比例方法作一省称,似亦可呼为腹民。